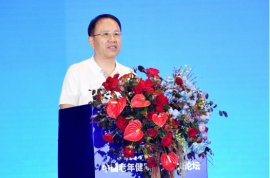年老身体机能衰退,人人有之,但衰老感的产生,却因人而异。因为这种主观上的感觉并非单由身体变化所致,心理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。
进入老年,自然会想到老,也免不了谈到老,但每天把“老”字记在心头,挂在嘴上,则会加速衰老。
伯特兰·罗素是英国著名哲学家、逻辑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,享年98岁。他不仅学术成就颇丰,在养生方面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体会。
罗素在《论老之将至》一文中提到,他的外祖母虽年过8旬,仍然充满生活情趣,喜欢阅读通俗科学读物。罗素对她的处世之道十分赞赏,曾说“我难以相信她会有空去注意她正在衰老。我以为这便是永葆青春的诀窍”。
即使面对白发,自感衰老,也要善于自我疏导。“我见白发喜”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相传有几位老人聚会在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钓台,饮酒赋诗,以遣“老”怀。无奈几位老人心情不好,佳句难得,席间气氛悲凉。这时,一位仅能粗解文意的侍者见此情景,便索取纸笔,一挥而就,写诗四句:“人见白发愁,我见白发喜。父母生我时,唯恐不及此。”诸老见后,欣然搁笔,笑而赞曰:“是极,是极!有此一诗,我们不必苦吟了,喝酒,喝酒!”
为何诸老对此小诗如此叹服呢?此诗文句虽然浅近,但含义却很深远。谁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白头到老,获得长寿呢?当年诞下的婴儿,经过漫长的人生历程,终于活到老年,见到白发银丝,怎不可喜呢?又有什么可愁的呢?
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《春日览镜有感》,也让人颇受启发。这首诗首句“习气不解老,壮心故嵯峨”,先写诗人本不知老,壮心犹在;后又写“今朝镜中逢,憔悴如枯荷”,说待到观镜照看,才发现衰象毕露,老之已至;后面却说“但淬割愁剑,何须挥日戈”,可见诗人并不为衰老的愁苦所困扰,因为时光不可倒转,追悔无益,应当宽怀解愁,磨好这把“割愁剑”,割断愁情,振奋精神,与儿童竞相欢歌旋舞,兴致勃勃,老而复健,又焕发青春的活力,所以诗人最后写道:“儿童竞佳节,呼唤舞且歌。我亦兴不浅,健起相婆娑”。
的确,老而又忘老,老来添童趣、怀童心,就是养生的妙法,就是长寿的诀窍。